温馨提示:这篇文章已超过676天没有更新,请注意相关的内容是否还可用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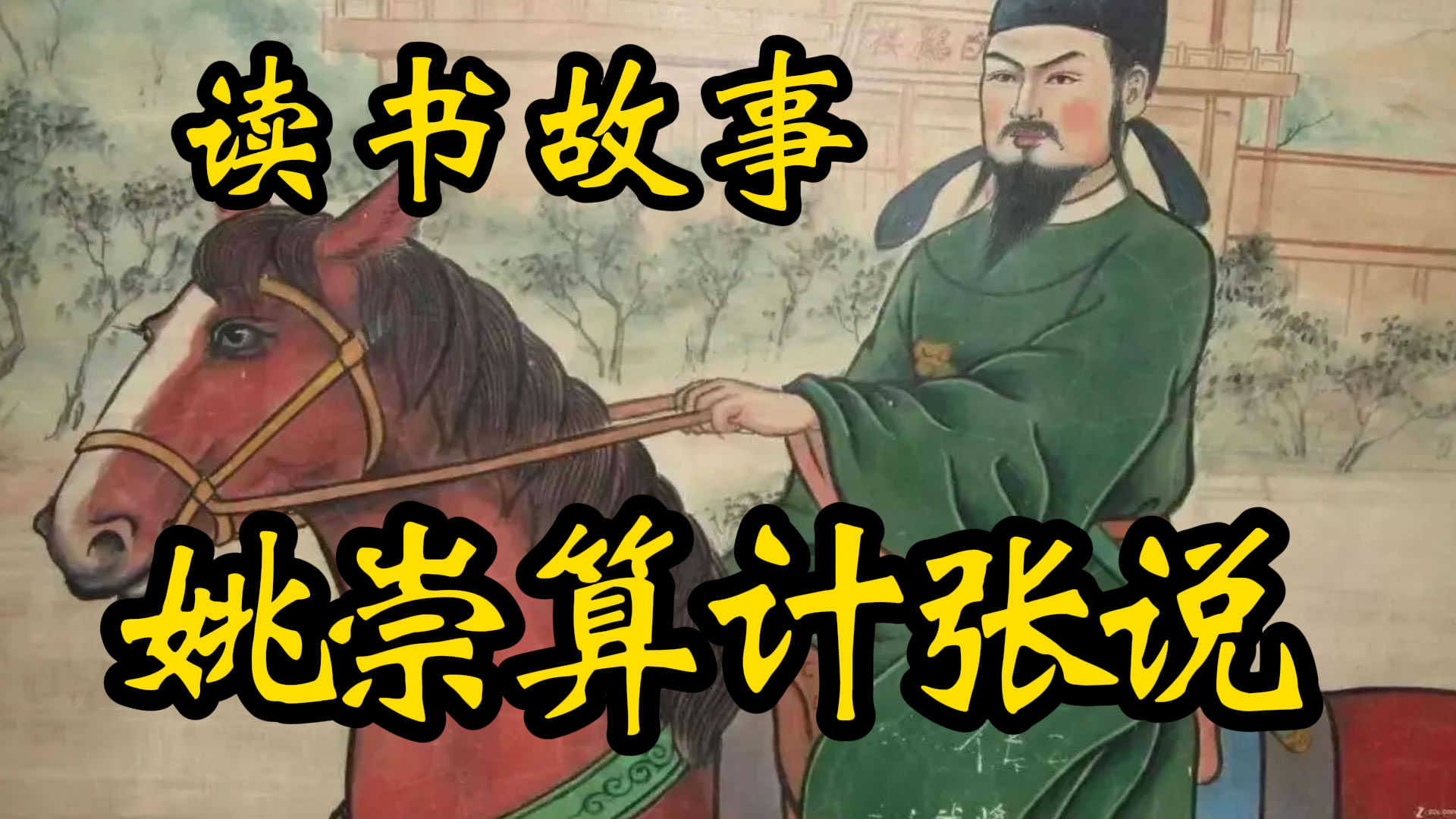
唐代开元年间,姚崇和张说均为朝中宰相,然而两人却因政见不同,积怨颇深。
早在武则天时期,姚崇就出任宰相并深得武则天赏识;武则天倒台后,他又被唐睿宗召回再任宰相;此后,他又被李隆基看重继续延续辉煌人生。
同朝为相的张说一直视姚崇为自己的政敌,生怕他影响自己的权力。因此,张说多次阻挠姚崇为相,两位宰相明争暗斗的角逐就此开启。
很快,张说就被姚崇抓住了一个机会。
一次,张说偷偷跑到岐王李隆范家中倒苦水,不料这件事让姚崇知道了。如果兄弟和睦,张说的举动自然不会有什么令人猜疑的地方,偏偏是唐玄宗继位后,对于几个兄弟都很忌惮。
毕竟玄宗皇帝的大哥宋王李成器,二哥李成义,弟弟岐王李隆范,诸多王爷们,在朝中势力很大,都有自己的影响力。就算这些兄弟没有夺位之心,但有时候也招架不住权臣、身边人的撺掇和煽动。因此玄宗一方面极力维护兄弟之情,另一方面削弱亲王实权,让他们断绝与朝中大臣的往来。
姚崇深知想要自己安然无恙,和张说的“对决”不可避免。于是他抓住张说前去李隆范家的把柄,并将这件事告诉李隆基。
翌日,姚崇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宫,唐玄宗见状问其怎么了?姚崇说:“臣非心病,而是心病”。于是,姚崇将自己担忧的张说私自前往李隆范家的事情说了出来。
听罢姚崇的说辞,李隆基当即就警觉了起来。姚崇之所以这样做,就是利用了李隆基对亲王和权臣走太近而威胁自己皇权的敏感、猜忌才打出了这样一张牌。忧虑加重的李隆基只能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。
利用他人的软肋、疑心,进而达成自己的目的,姚崇的手段和智慧,可见一斑!姚崇不仅仅是政治才能卓越,在为人处世方面,可以说是唐朝一众宰相中的天花板。生前能辅政,死后还能保家。
姚崇于开元九年病逝,时年七十二岁。
眼见自己回天乏术,在自己病种时,姚崇便立下遗嘱,阐明信佛之害,不许子孙为他延请僧道,追荐冥福。
等到临终时,姚崇又叮嘱自己的儿子们,说道:“我任宰相多年,所言所行,多可传诵后世。死后的碑文,不是著名文家不写。当今文坛巨匠,首推张说,我和他素不相睦,若去特地求他为我撰写碑文,他必然不从其请。我留下一计,在我灵座之前,陈设珍贵玩物,俟张说来吊奠,细察其情。他若见到这些珍玩,不屑一顾而去,是他记挂前仇,防他报复,汝等速离此地回归乡里。倘他逐件玩弄,有爱慕之意,汝等可传我遗命,悉数奉赠。即求他作一碑铭,以速为妙!待他碑文做就,随即刻于石碑,并将原稿进呈皇帝御览。我料张说性贪珍宝,使其利令智昏必然就范。切记照此办理,以快为妙。他必事后追悔索回文稿。果能如我所料想的那样,碑文中一定赞誉我的平生功业,后想寻隙报复,难免自陷矛盾之境,没法寻衅了。”
姚崇的儿子姚彝、姚异等人谨记父命,遍讣丧文,设灵接受百官吊唁。
张说入朝奏事闻姚已殁,顺道往吊。姚崇诸子依父命早已摆列珍玩,张说入吊后,双手扶摩诸物,极表爱慕之意。
姚彝等人当即叩请说:“先父曾有遗命,谓同僚密友肯为撰写碑文者,当以遗珍相赠。大人乃当代文坛耆宿,倘若不吝赐文,以记先父之履历,当以诸物相赠。”
张说欣然允诺,彝等促其从速撰写。
张说兴致极佳,当即撰文,为姚崇写了一篇淋漓尽致的颂德文章。
文一落笔,姚家就送来珍玩,取走碑文,连夜雇请石工,刻之于石,并即日将原文进呈御览。
玄宗看了铭文,连声称赞“写得好,写得好。似此贤相,不可无此贤文。”
张说一天以后,省悟过来,暗想自己与姚崇有隙,多年不睦,如何反去颂扬其德呢?连忙派人索还原稿,托言文字草率,须加工润色。
不料使者回报已刻成碑文,并呈御览。张说连连顿足,抚着胸叹息说:“这是姚崇的遗策,我一个活张说,反被死姚崇所算计,真觉羞愧啊!”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